
清早采回带露的松针
把萤火虫的旧灯盏擦亮
小蝴蝶等在原野尽头
用泪水打湿的翅膀撑起小伞
我就要去远方了
白云深处听山歌
悬崖峭壁品蜂蜜
在人去楼空的庭院
燕子飞入石头的洞穴
在秦岭与巴山架起桥梁
界碑矗立在无界的岭上

下得山来,经过村口那棵大树时,三妹急切地说声“二姐等等”,然后就撒腿飞奔至树下,拜了又拜,抱了又抱,一定是在祈求大树爸爸保佑我们三姊妹都平平安安。

“你们仔细看,看到啥东西了吗?”大叔指着悬崖,笑着问。
我们昂起头,瞪大眼睛望了好半天,也没望出啥名堂来。
“看仔细些,看到那些洞子了吗?”大叔又提醒我们。
“啊,看到了!看到了!”就在高耸的光秃秃的悬崖峭壁上,确实有一些黑黑的东西不规则地点缀着,如果不是大叔提示,我们绝对猜不到那是一个个洞子。
“这些洞子都是人工开凿的,每个洞口摆放着木箱,里面居住的就是高山中蜂。”

工人们纷纷摇头,表示都没听说过这么个人:“秦巴山区的修路人成千上万,来的来,去的去,别说几年前,就是几天前都在换人呢。”
“那……那换的都是活人,死人不可能很多吧?”三妹的眼里涌出泪水,“我爸爸死在高速路工地上了,被沙土埋了……”
现场陷入惊愕和沉寂之中,空气似乎凝固了。片刻后,一位年长的大叔拍拍脑袋,突然恍然大悟般:“哦,我想起来了,马文山,是有这么个人。”大叔黝黑的脸庞配上圆圆的大鼻头,和善中自带几分滑稽。
“我记得他瘦高个子,戴个黑框眼镜,挺斯文的。”旁边一个小个子青年接过话茬。
“嗯,我爸爸长得是挺帅的,不过没戴眼镜。”三妹纠正道。
“对对对,我也想起来了,”一个长着娃娃脸的胖大叔说,“马文山会唱山歌,每次干完活歇气,他都要唱支山歌给大家解乏。”
“嗯,我爸爸唱歌好听得很,他喜欢唱《春天里》。”三妹说。
“文山哥性格活跃,喜欢开玩笑,”刚才那个板寸头青年挠着头,不好意思地说,“我记得他喜欢从背后蒙住人的眼睛,让人猜他是哪个。”
“嗯,我爸爸就爱那样,他最喜欢把我抛起来,举高高。”
工友们七嘴八舌,纷纷说起“记忆中”的筑路工友马文山。他们的“记性”真好,几年前的事都没忘记,虽然偶尔也会记错。
三妹开心极了,原来这么多人都记得她的爸爸。他们曾在过去的岁月里和爸爸朝夕共处,亲密无间;他们现在正做的工作,爸爸也曾经做过;他们穿着的工装,爸爸也曾经穿过。这些大叔多么和善多么亲切呀,和他们交流,感觉就像又和爸爸在一起了,爸爸还活着呢。
授权给中国少年儿童出版总社《儿童文学·选萃》杂志2024年3月刊《大树的女儿》一次性非专有使用

哇,还真是呢,从巫山那边飘来的云雾,一旦抵达陕西地界,立马就烟消云散了,形成一条明显的分界线,一边是云雾缭绕的重庆,一边是阳光普照的陕西。人们把这一奇观趣称为“阴阳界”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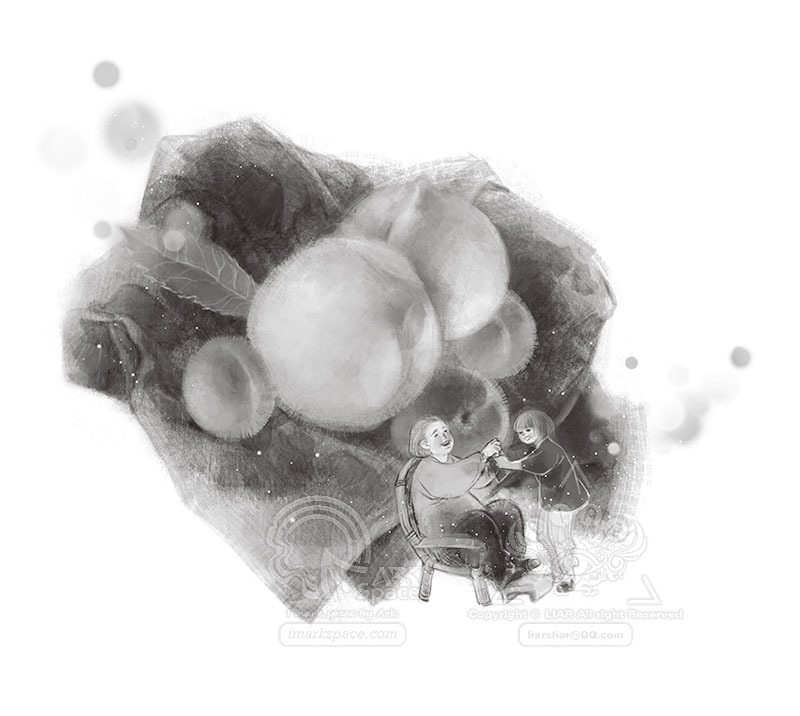
“还没熟呢,吃不得。”光看那果子品相,我就晓得桃子酸,李子苦。
“不吃,就留个纪念。”
我不再说啥,三妹向来是个重感情的人。
“我要拿回家,送给太奶奶。”三妹低头把果子揣进书包,轻声说,“我要告诉她老人家,一百年前的树,还在结着一百年后的果子。”

山外是山,天外是天,世界之外还是世界。
这时,三妹突然喃喃地说:“二姐,我现在晓得了,我们流的血、泪、汗为啥是咸的?”她的声音听上去有种梦呓的感觉,“老先人背盐时,盐都渗进他们的血肉里了。”
我吃了一惊,扭头望着八岁的妹妹,她的眼里有泪光闪烁。想清这个问题,也许用了她八年时间,也许只是一瞬间的事情。
“二姐,你上次说我们身体里藏得有盐巴,你说得对,但盐巴不是天生就有的,而是老先人拿命换回来的。”三妹停顿片刻,抿了抿嘴,继续说道,“只有当我们流泪了,流汗了,流血了,藏在身体里的那些盐巴,才会又重新还给老先人。”
三妹说得有道理。为啥每当我们流泪,流汗,流血时,总会想起老先人呢?因为在那些时刻,先人们确实会重新活过来,活在我们的心里。 最后一缕残阳拖着云彩的暗影,在洞口稍做停留后,便决然隐退。
授权给中国少年儿童出版总社《儿童文学·选萃》杂志2024年4月刊《大树的女儿》一次性非专有使用





Comment | 最新评论